|
科學的矛盾心理
20世紀以來,沒有沉重歷史包袱的美國,雖然取得了經濟繁榮,但科學技術的基礎遠不如歐洲。可現在機會到來了,歐洲一大批在科學史上舉足輕重的核科學家,因為“忍受不了苛刻的限制,連續的爭吵和種族的歧視、鎮壓與痛苦。”紛紛背井離鄉來到了當時中立的自由之邦——美利堅合眾國。這是輸入美國的無價之寶,是新的真正的財富,有了人才,就有了一切。歐洲的人才與美國的工業相結合是很了不起的。
集中到美國的歐洲科學家出于對歐洲局勢的憂慮和對希特勒的仇恨,他們一反17世紀科學家的宣言,要讓科學成果為政治軍事服務。
核登上社會舞臺的序幕就是以爭取和平的姿態出現的。
哈恩的實驗發現鈾核裂變以后,匈牙利青年物理學家西拉德,這時已遷居美國,他敏銳的想象力,清晰地意識到了將來可能要開展一場原子武器的競賽。他說服了費米及美國的同行們實行保密,提出對本身的研究工作進行自我約束。
西拉德在1939年2月給約里奧·居里的信中寫道:“兩星期以前,當哈恩的文章傳到我們這里來的時候,我們這里就有些人想了解:鈾裂變以后能否有中子釋放出來。如果能有一個以上的中子釋放出來,那么就有可能形成鏈式反應。在一定的條件下,制造對人類有極大威脅的原子彈是有可能的……我們但愿中子根本不能釋放出來,或者就是釋放出來也是微不足道的,這樣就不必為這一問題而擔心了。”他請求約里奧·居里不泄露研究成果。
這是科學有史以來最奇怪的現象,科學家的功能就是在求得科學的進步,將“不能”變為“可能”;現在卻因為科學的進步會帶來嚴重后果,竟然希望科學不要繼續,實驗不要成功。這充分說明,科學在與道德發生沖突的時候,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感在行為中反映出的矛盾心理。
 西拉德請求約里奧·居里立即通知他關于不泄露研究數據的問題是否達成了協議,并表明對這一問題所持的態度。但是,西拉德沒有接到回信。其時,約里奧·居里研究小組,已經接近了西拉德所擔心的那種鏈式反應了。由于種種原因,約里奧·居里將西拉德的建議置于一旁,卻將自己完成的實驗結果寄給英國的《自然》雜志發表。 西拉德請求約里奧·居里立即通知他關于不泄露研究數據的問題是否達成了協議,并表明對這一問題所持的態度。但是,西拉德沒有接到回信。其時,約里奧·居里研究小組,已經接近了西拉德所擔心的那種鏈式反應了。由于種種原因,約里奧·居里將西拉德的建議置于一旁,卻將自己完成的實驗結果寄給英國的《自然》雜志發表。
西拉德知道自己的努力失敗以后。也只好違背自己的意愿同意發表他在鏈式反應方面的研究材料(同一個時期完成鏈式反應實驗的除約里奧·居里、費米、西拉德之外,還有N·玻爾等)。
很快,《自然》雜志、《物理評論》都先后報道了鈾裂變時能釋放出多余的中子。因此鏈式反應可以自持下去,從而也就能實現核爆炸。
從1939年4月末到7月末,西拉德、維格納、泰勒(都是匈牙利的流亡物理學家)和維斯科普(奧地利的流亡物理學家)一直設法讓美國政府了解原子能研究工作的重大意義。早先,費米就曾憑哥倫比亞大學系主任喬治·波格拉姆的介紹信去拜訪了海軍軍械部長、海軍上將胡伯,同他討論了制造原子彈的可能性。但這位部長只表示了禮節上的興趣,希望費米繼續提供發展情況,而實際上卻未予重視。
在歷史還沒有真正充分地認識到科學的作用時,科學只能仰仗于權力。生活在這個時代的科學家,同樣還難以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,他們需要花精力找門路,學會奔走呼號,聲明主張,宣傳自己工作的意義,尋求權力支持和財力投資。
 德國混亂的科研管理
致羅斯福的信 德國混亂的科研管理
致羅斯福的信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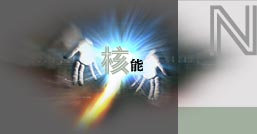

 西拉德請求約里奧·居里立即通知他關于不泄露研究數據的問題是否達成了協議,并表明對這一問題所持的態度。但是,西拉德沒有接到回信。其時,約里奧·居里研究小組,已經接近了西拉德所擔心的那種鏈式反應了。由于種種原因,約里奧·居里將西拉德的建議置于一旁,卻將自己完成的實驗結果寄給英國的《自然》雜志發表。
西拉德請求約里奧·居里立即通知他關于不泄露研究數據的問題是否達成了協議,并表明對這一問題所持的態度。但是,西拉德沒有接到回信。其時,約里奧·居里研究小組,已經接近了西拉德所擔心的那種鏈式反應了。由于種種原因,約里奧·居里將西拉德的建議置于一旁,卻將自己完成的實驗結果寄給英國的《自然》雜志發表。